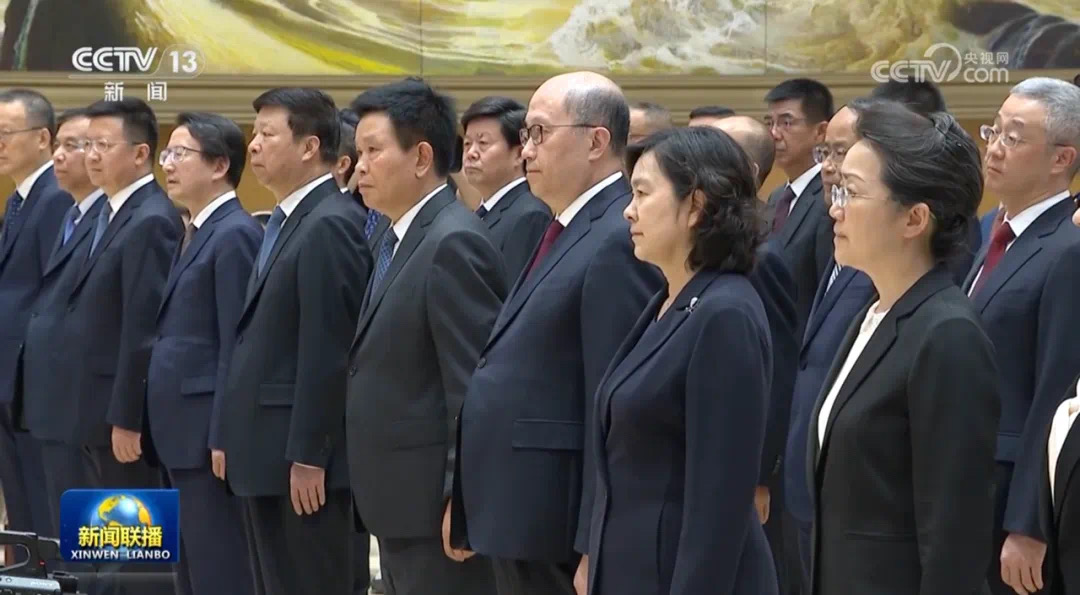这才是明朝灭亡的真实原因,历史教训令人深思!
来源:文化纵横
作者:朱永嘉 |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
▍明何以兴——朱元璋的反贪污斗争
明代是在推翻元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,我们知道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贪腐的 地在绛,属河东地区。《汉书·周勃传》云:
岁余,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,绛侯勃自畏恐诛,常被甲,令家人持兵以见。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,下廷尉,逮捕勃治之。勃恐,不知置辞。吏稍侵辱之。勃以千金与狱吏,狱吏乃书牍背示之,曰“以公主为证”。公主者,孝文帝女也,勃太子胜之尚之,故狱吏教引为证。初,勃之益封,尽以予薄昭。及系急,薄昭为言薄太后,太后亦以为无反事。文帝朝,太后以冒絮提文帝,曰:“绛侯绾皇帝玺,将兵于北军,不以此时反,今居一小县,顾欲反邪!”文帝既见勃狱辞,乃谢曰:“吏方验而出之。”于是使使持节赦勃,复爵邑。勃既出,曰:“吾尝将百万军,安知狱吏之贵也!”
“勃以千金与狱吏”,那不是狱吏受贿吗?这事实上是司法系统贪腐的问题。周勃在狱中,还不就是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曾说过的“猛虎处深山,百兽震恐,及其在阱槛之中,摇尾而求食,积威约之渐也”。(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)周勃要脱身,只能放下身段,求助于狱吏。
历朝历代因贪腐而衰亡的案例甚多,唐玄宗由开元到天宝,任用的李林甫和杨贵妃之兄杨国忠作宰相,他们还不都是大贪官嘛,最终引起安史之乱,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。
朱元璋早年在游方僧生活过程中,“人之情伪,亦颇知之”。这“人之情伪”是指元末官吏贪污腐败之恶,他亲身经历过。元末明初叶子奇在《草木子·杂俎篇》讲到:
官贪吏污,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。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:所属始参曰拜见钱,无事白要曰撒花钱,逢节曰追节钱,生辰曰生日钱,管事而索要曰常例钱,送迎曰人情钱,勾追曰赍发钱,论诉曰公事钱,觅得钱多曰得手,得除美州曰好地分,补得职近曰好窠窟。
其实这些语言,如今仍在民间流行,若“送人情”、“得手”等词语。元末这样的结果便是:“上下贿赂,公行如市,荡然无复纪纲矣。肃政廉访司官,所至州县,各带库子检钞秤银,殆同市道矣。《春秋》传曰,国家之败,由官邪也。官之失德,宠赂彰也。岂不信夫。”
由于朱元璋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社会现实,所以他对官僚机构的吏治情况都抱怀疑的态度,因而强调“俗儒多是古非今,奸吏常舞文弄法,自非博采众长,即与果断,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”。故其在惩治贪腐、整顿吏治上用的手段非常狠毒(严苛)。

朱元璋在《大诰》的第三条《胡元制治》讲到元代的地方官达鲁花赤们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的情况:
人事不通,文墨不解,凡诸事务,以吏为源,文书到案,以刊印代押,于诸事务忽略而已,此胡元初治焉。三十年后,风俗虽异,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者,略不究心,施行事务,仍由吏谋,比前历代贤臣,视吏卒如奴仆,待首领官若参谋,远矣哉!朕今所任之人,不才者众,往往蹈袭胡元之弊,临政之时,袖手高坐,谋由吏出,并不周知,纵是文章之士,不异胡人,如户部侍郎张易,进以儒业,授掌钱谷,凡诸行移,谋出吏,己于公廨袖手若尸,入奏钱粮,概知矣。朕询明白,茫然无知,惟四顾而已。吁!
用现代的话来说,官僚们一切工作,都是靠其秘书班子具体操作,如果追问所以然,则“茫然无知”。朱元璋对于这种情况异常不满,所以在他心目中户部是分管钱粮出入的部门,其中必有弊端。
他为什么如此关心户部这个系统?因为税粮的出入收支关系到王朝的生命线,王朝庞大的支出是靠它来维系的,故朱元璋的反贪污斗争就先从这个部门开刀。
明朝的第一大案是空印案,这次没有抓到要领,因为空印是报销钱粮的收入要与户部的数字核对,地方上缴的钱粮,要与户部的账单统一,需要先盖印章,到户部核对数字后再填上数字,仅凭空印治罪,根据不足。
朱元璋大规模治贪的案件,从郭桓案开始。郭桓的职务是户部侍郎,是分管税务的负责人,起因是他账面上的数字与实收的数字之间有巨大的差额,朱元璋怀疑他有贪污的嫌疑。
朱元璋查贪污案有一个特点,喜欢寻根问底,不仅查贪污者,还要追问贿从哪儿来的,不仅查受贿之人,而且查行贿的人,行贿者的钱款从哪儿来的,如此一级又一级往下查,那牵涉的人便很多了。
《大诰》有一篇文字的题目为《问赃缘由》,是《大诰》的第二十七条,其云:
如六部有犯赃者必究,赃自何而至,若布政使贿于部,则拘布政使至,问斯赃尔自何得?必至于府,府亦拘至问赃何来。必至于州,州亦拘至,必至于县,县亦拘至,必至于民。至此之际,害民之奸,岂可隐乎?其令斯出,诸法司必如朕命,奸臣何逃之有哉?呜呼!君子见而其政尤勤,小人见而非心必省。
这是朱元璋口谕的记录,如果真要认真执行起来,反贪必能彻底,因为中国的官僚机构是层级式的,由一个赃案如此往下追的话,自上而下,就能查出很多问题。这样做有一个好处,受贿者与行贿者统一处理,行贿者的目的是因贿而获利。
当反贪污有一个打击行贿与受贿两个方面这中间应有区别,弄清楚行贿者是主动还是被迫,行贿后是否获利,也许能缩小打击面。其造成的后果不同,赃款的来源不同,行贿以后的后果也不同。若是工程项目,如果行贿的目的是为了偷工减料,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。
若出于无奈,是从自己正当的收入中挤出来的,那又当别论,被迫与主动也要具体分析。这是当今反贪污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。如果只查贪官,不查行贿者,只处分贪污者,不处理行贿者,那么贪污很难根除。
贪污与行贿二者互为因果,其各自所处情况也不相同,需要有分析地处理才能恰到好处,如朱元璋那样一味蛮干,打击面就太大了。
郭桓案的起因见《大诰》第二十三条,题为《卖放浙西秋粮》:
户部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,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,其郭桓等止收陆拾万石,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,以当时折算,可抵二百万石,余有一百九十万未曾上仓。其垣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伍拾万贯,致使府县官黄文等,通同刁顽人吏沈原作弊,各分入己。
从郭桓案可以看到,不仅财税系统是如此,在地方上的行政官僚系统同样如此,实际处理日常事务的是吏胥,科场上出身的官僚们没有实际事务工作的能力和经验,所以他们离不开吏胥的实际操作。
吏胥之间都是同乡同籍,有的甚至世代相传,故积弊很深。郭桓案是朱元璋编《大诰》的动因,目的是以当时的案例来警示在位的官僚队伍。《大诰》始于洪武十八年(公元1386年)冬,朱元璋御制序是在十月初一,刘三吾的后序在十月十五日,实际操作应在十一月初。
续编颁行的时间是在次年年中,三编颁行的时间应在洪武二十年(公元1388年)的二月,《武臣诰》是洪武二十年的十二月,这四篇《大诰》共计有二百三十六个条目,都是当时的案例。从文体上讲有三类,一是案例,二是朱元璋的训诫,三是峻令。
朱元璋颁行四篇《大诰》的目的是整顿吏治,通过大量严厉治贪的案例以达到“警省愚顽”的宣教作用,其中有不少朱元璋极其口语化的教谕。可见这二年是朱元璋亲自参预的反贪污运动,其中还有不少朱元璋与案犯的直接对话。
从总体上讲,朱元璋那样严厉的治理贪污的运动没有持续下去,而是逐渐松懈了。尽管朱元璋在《大诰》中称“斯令一出,世世行之”,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明成祖时,各类问题又重新出现,仁、宣之后,到了宪宗、孝宗、武宗时,各种危机逐渐露头。
明代的积弊仍然是“官不留意政事,一切付之吏胥”,如明代户部的十三司,不许江浙人为之,但十三司的胥算却都是绍兴人。嘉靖、万历年间,从上到下,贪污之风盛行,严嵩及其子严世藩便是大贪污犯。
到了万历年间,贪官更多,那些大宦官个个都是嗜财如命,整个朝廷在位执政者,权力在手,很少有不贪的。明熹宗时,魏忠贤更是横行不法,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,哪个不是贪官啊!
▍明所以亡——亡在贪官身上
顺天府尹刘宗周曾上疏言:“顷者,特严赃吏之诛,自宰执以下,坐重典者十余人,而贪风未尽息,所以导之者未善也。”一方面可以看到贪风之盛,另一方面没有找到治贪的根本措施,而重用的又是贪官。明代的末代皇帝崇祯帝时,辽东问题越来越严峻,军饷成了国家最大的开支,辽东失守,一个重要的原因,士兵拿不到军饷。为什么士兵缺饷呢?
与军饷被大大小小的贪官克扣有关。另一个方面,是西北的边军也拿不到军饷,士兵哗变,与饥饿的农民结合。如李自成原来是西边的驿卒,后被裁撤而参加农民起义,张献忠的出身就是边军。这样崇祯帝时期,明王朝不得不同时两面作战,明王朝怎能不亡呢?
明末为了辽饷,不得不开始在全国原有税银基础上前后三次加派饷银,弄得民不聊生,加上多年严重的旱灾,农民不得不四处流亡,西北地区民不聊生的情况更为严重,这是大规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社会基础。崇祯身边受其信用的是如温体仁那样的贪官污吏,明王朝怎能不坍塌呢?
崇祯十七年(公元1644年)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明亡前不得不下“罪己诏”,其中有这么几句话:
至于任大臣而不法,用小臣而不廉,言官首窜而议不清,武将骄懦而功不奏,皆由朕抚驭失道,诚感未至。终夜以思,局蹐无地。(《明季北略》卷二十《十一颁罪己诏》)
崇祯帝最终吊死在煤山的树上,我前几年到北京时还去参观过。崇祯帝上吊时,在衣襟上书曰:
“朕凉德藐躬,上干天咎,致逆贼直逼京师,皆诸臣误朕。朕死无面目见祖宗,自去冠冕,以发覆面,任贼分裂,无伤百姓一人。”(《明通鉴》卷九十)
对明末的官僚队伍,也要持分析的态度,贪官污吏固然不少,但也有不少宁死不屈而殉难者,问题是崇祯帝不识人,分不清好歹。崇祯元年(公元1628年)十二月,他杀袁崇焕,便错杀了好人,这又与大贪官温体仁有关。《明史·袁崇焕》记载,袁崇焕,字元素,东莞人。
万历四十七年进士,授邵武知县。此人好谈兵,而且喜欢自己作调查研究。天启二年赴京朝觐,被擢为兵部职方主事,时辽东广宁师溃,他单骑赴辽东作实地调查,人不知其所踪。“还朝,具言关上形势”,夸下海口说:“予我军马钱谷,我一人足守此。”
于是超擢为兵部佥事,监关外军,发帑金二十万,听其招募军队。当时辽东是王在晋负责,让袁崇焕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,崇焕即夜行,以四鼓入城,王在晋题其为宁前兵备佥事。十三山难民十余万,久困不能出,大学士孙承宗行边,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。
于是崇焕内附军民,外饬边备,劳绩大著。孙承宗决定让袁崇焕守宁远,崇焕定规制,城高三丈二尺,雉高六尺,址广三丈,上二丈四尺。天启五年夏,孙承宗与袁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及大小凌河,缮城郭居之。“自是宁远且为内地,开疆复二百里。”
天启六年正月,清兵渡辽河,二十三日抵宁远,崇焕誓死守,迁城外民居,携守具入城。次日,清兵大举进攻,崇焕令闽卒在城上发西洋火炮,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中,重伤而死,宁远遂解围。这便是当时的宁远大捷。
之后袁崇焕由于与魏忠贤不合而乞休,天启七年七月允其归休。不久,熹宗去世,崇祯即位,阉党败,魏忠贤伏诛,于是廷议又请召崇焕。其年十一月擢右副都御史,崇.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,督师蓟、辽,兼都登、莱、天津军务。
七月,崇焕入京,崇祯帝召见平台,咨以方略,袁崇焕说了这么一番话:“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,调众口不足。一出门,便成万里,忌能妒功,夫岂无人,即不以权力掣臣肘,亦能意见乱臣谋。”崇焕以前此熊廷弼、孙承宗皆为人排搆,不得竟其志,上言:
恢复之计,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,以辽土养辽人,守为正著,战为奇著,和为旁著之说。法在渐不在骤,在实不在虚。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。至用人之人,与为人用之人,皆至尊司其钥。何以任而勿贰,信而勿疑?盖驭边臣与廷臣异,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,但当论成败之大局,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。事任既重,为怨实多。诸有利于封疆者,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况图敌之急,敌亦从而间之,是以为边臣甚难。陛下爱臣知臣,臣何必过疑惧,但中有所危,不敢不告。
在战事紧迫之际,要做到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,在君王与边将之间直接沟通信息,在那时确有难处,而崇祯又是一个多疑的人。《荀子·议兵》:“兵者,以食为本。”《管子·权修》:“地之守在城,城之守在兵,兵之守在人,人之守在粟。”
可见那时作战胜败决定于军饷能不能充分保障,士兵要有粮饷,吃饱了才能打仗。明末饷源不足,再加上内外贪污成风,边兵怎能打仗呢?袁崇焕到了辽东,关键还是军饷的问题。
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矛盾的焦点就是争夺饷源,袁崇焕受崇祯怀疑的原因,同样也是饷源的问题,加上皇太极利用被俘的宦官搞反间计,结果崇祯错杀了袁崇焕,自坏长城。西部农民起义,士兵哗变,也与饷源不足和长期欠饷问题有关,明朝末年上下贪污成风,加剧了军饷的困难,在这种内外矛盾交织下,明朝的灭亡无法避免。
下面先说一下皮岛的毛文龙与袁崇焕之间的矛盾,问题的根源在于军饷。《明史》把毛文龙传附在袁崇焕传的后面,计六奇《明季北略》中的叙述更加详细一些。崇祯元年八月间,袁崇焕返回辽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戍守宁远的川、湖兵因缺饷四个月而大譟,余十三营起而应之。
袁崇焕抓了首恶十五人戮于市,事定以后,要保持军兵在辽东地区的战斗力,军饷是一个实际问题。当时辽西的军饷要经过登莱,在海上经毛文龙的皮岛,然后才能到达辽西,而辽西的军饷被毛文龙克扣下来,留在京师贿赂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,这样毛文龙与袁崇焕为了辽西的军饷,便有矛盾了。袁崇焕杀了毛文龙,要回辽西的军饷,也断了京师大小贪官污吏的财源,正是他们最后促使崇祯杀了袁崇焕。
毛文龙是浙江人,从都司援朝鲜,逗留在皮岛,皮岛的位置在鸭绿江口,辽东失守以后,辽人退至渤海沿岸诸岛,毛文龙设法在这些沿海岛屿设置军政机构。计六奇《明季北略》卷二《毛文龙入皮岛》条称:
文龙谋择一岛驻军,以截清兵。李景先曰:“莫如皮岛,大可四百里,环山峭壁。”文龙北行五百里,至岛,荒茸无人,多蛇虎,悉射杀之,遂迁居于中。此天启二年五月也。已而,闻杀清之大将哈都,辽民归者万计。天启三年,文龙与诸将计曰:“辽东要地,惟金州南通旅顺口,北至三牛坝,西通广宁,东可图复。此城若得,陆扼建州骑,水可登州运粮、停泊。”遂命守备张盘、程鸿鸣等,率众自麻羊岛往,止距海面四十里。
毛文龙的军队以辽东人为基本群众,成为明朝联络朝鲜、从东面牵制后金的一支力量,故明朝与后金都想对他进行争取。《明季北略》卷二《毛文龙安州之战》条称:
天启四年七月初二,遣人与龙议和。李永芳致手札,言龙在辽族属未遭屠戮者,尽行优待,诱龙同叛,中分土地等情。文龙将来使暨手札差官进呈。上加左都督,赏大红蟒衣一袭,银五十两。
《明季北略》卷三《毛文龙请饷》条称:
兵须用五万,今臣有浙直等处南兵八千,挑选辽兵三万七千,招练辽兵二千,已四万七千矣。以五万兵计,一岁之饷,并军器、盔甲、马匹、船只等项,应一百五十万两方能足用。自有东事,海内加派新饷,每岁四百万,足供今日山海之用矣!尚有辽饷旧额每岁一百万,今全辽已亡,此项银两所当给臣者也。三年以来,止给银十一万两、米二十万石,其够养官兵、够养马匹乎?
这里值得注意的是,“辽饷旧额每岁一百万,今全辽已亡,此项银两所当给臣者”,这句话导致原本属于辽西的银两就没有了,都到了毛文龙那里。袁崇焕在崇祯元年八月去宁远时,第一个问题便是宁远欠饷导致军队哗变,要守辽西便有饷银来源的问题,这是袁崇焕与毛文龙矛盾的根子。
在袁崇焕心目中,毛文龙在海上牵制不了后金,反而靡饷无算。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称:
顾文龙所居东江,形势虽足牵制,其人本无大略,往辄败衄,而岁糜饷无算;且惟务广招商贾,贩易禁物,名济朝鲜,实阑出塞,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,有事亦罕得其用。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,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,治兵关、宁。兵部议不可,而崇焕心弗善也,尝疏请遣部臣理饷。文龙恶文臣监制,抗疏驳之。
为什么兵部议不可撤掉毛文龙呢,因为兵部尚书梁廷栋受了毛文龙的贿赂,故其偏向毛文龙,而袁崇焕建议遣部臣理饷,实际上是限制毛文龙,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,促使袁崇焕下定决心对毛文龙采取措施。
至是,遂以阅兵为名,泛海抵双岛,文龙来会。崇焕与相燕饮,每至夜分,文龙不觉也。崇焕议更营制,设监司,文龙怫然。崇焕以归乡动之,文龙曰:‘向有此意,但惟我知东事,东事毕,朝鲜衰弱,可袭而有也。’崇焕益不悦。(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)
两个人谈不拢,毛文龙既不愿受约束,也不愿放下兵权还乡里去,那似乎就只有杀了。《明史•袁崇焕传》载:
以六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,先设幄山上,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幄外。文龙至,其部卒不得入。崇焕曰:“予诘朝行,公当海外重寄,受予一拜。”交拜毕,登山。崇焕问从官姓名,多毛姓。文龙曰:“此皆予孙。”崇焕笑,因曰:“尔等积劳海外,月米止一斛,言之痛心,亦受予一拜,为国家尽力。”众皆顿首谢。
崇焕因诘文龙违令数事,文龙抗辩。崇焕厉色叱之,命去冠带絷缚,文龙犹倔强。崇焕曰:
“尔有十二斩罪,知之乎?祖制,大将在外,必命文臣监。尔专制一方,军马钱粮不受核,一当斩。人臣之罪莫大欺君,尔奏报尽欺罔,杀降人难民冒功,二当斩。人臣无将,将则必诛。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,大逆不道,三当斩。每岁饷银数十万,不以给兵,月止散米三斗有半,侵盗军粮,四当斩。擅开马市于皮岛,私通外番,五当斩。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,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,走卒、舆夫尽金绯,六当斩。自宁远还,剽掠商船,自为盗贼,七当斩。强取民间子女,不知纪极,部下效尤,人不安室,八当斩。驱难民远窃人参,不从则饿死,岛上白骨如莽,九当斩。辇金京师,拜魏忠贤为父,塑冕旒像于岛中,十当斩。铁山之败,丧军无算,掩败为功,十一当斩。开镇八年,不能复寸土,观望养敌,十二当斩。”
数毕,文龙丧魂魄不能言,但叩头乞免。崇焕召谕其部将曰:“文龙罪状当斩否?”皆惶怖唯唯。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,崇焕叱之曰:“文龙一布衣尔,官极品,满门封荫,足酬劳,何悖逆如是!”乃顿首请旨曰:“臣今诛文龙以肃军。诸将中有若文龙者,悉诛。臣不能成功,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。”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。乃出谕其将士曰:“诛止文龙,余无罪。”
如果回过头来看,袁崇焕如此杀掉毛文龙,有点太匆忙了,处刑之前要审讯其口供,并提供具体事实依据。这十二条罪状过于简单,把事情弄清楚,并录下口供,然后把他押解到京师,让崇祯帝自己决断处置。
就以第一条罪状来讲,当时毛文龙之所以不让核实军饷收支,因为这是朝廷文臣武将贪污纳贿的财源,毛文龙所受军饷大部分留在京师贿赂朝廷大臣,内阁首辅的温体仁、兵部尚书梁廷栋都与之有牵涉。
温体仁本来就是一个贪官,崇祯元年时,御史毛九华弹劾称:“温体仁居家时,以抑买商人木为商人所诉,赂崔呈秀以免,又因杭州建逆祠,作诗颂魏忠贤。”
“御史任赞化亦劾体仁娶娼、受金,夺人产诸不法事。”(《明通鉴》卷八十一)温体仁与毛文龙是同乡,最终是温、梁二人后来五次上疏请杀袁崇焕,毛文龙背后有一条利益链在那儿,袁崇焕杀毛文龙断了他们的财路,这是他们要求杀掉袁崇焕的原因。
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之后,如何稳住皮岛这个地区的军队和将领,这个问题袁崇焕没有处理好,毛文龙一被杀,部队就失控了,后来发生孔有德、耿仲明叛降清军的事,对袁崇焕很不利。清皇太极对孔有德热情优礼,这也动摇了皮岛守军的军心。
此外,袁崇焕虽杀毛文龙,虑其部下为变,反而增饷十八万,其言:“东江一镇,牵制所必资。今定两协,马军十营,步军五,岁饷银四十二万,米十三万六千。”其结果是兵减饷增,引起崇祯的疑心。其实毛文龙的收入来源,不仅是兵饷,毛文龙被杀后,这个队伍的人心散了。
努尔哈赤死后,袁崇焕与皇太极有过和议的书信往还,而皇太极深知不除去袁崇焕,则很难消灭明在辽东的力量,遂设反间计。《明通鉴》卷八十一崇祯二年十二月载:
先是大军获宦官二人,令副将高鸿中等守之。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计鸿中等于二宦官前。故作耳语云:“今日撤兵,袁巡抚有密约,事可立就矣。”时杨太监者佯卧,窃闻其言,纵之归,以所闻告于上,上遂信之不疑。再召见崇焕及大寿于平台,诘崇焕以杀毛文龙之故,责其援兵逗留,缚付诏狱。成基命叩头请慎重者再,上曰:“慎重即因循,何益!”基命复叩头曰:“兵临城下,非他时比。”亦不省。
此前在皇太极忙于对朝鲜作战时,袁崇焕乘机恢复了锦州、大小凌河及松山、杏山、塔山地区的据点,加强了山海关外的防线,皇太极不得不改变战略方针,从西边直接入关,扰乱明辽西及山海关的后方,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,从根本上动摇袁崇焕辽西防线的根基。
在满人入关前,袁崇焕曾上疏称:“臣身在辽,辽无足虑,惟蓟门单弱,敌所窃窥,请严饬蓟督峻防固御。”一疏不省,再三疏之,却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。后金军是从青城出发,青城即大宁都司的新城卫,在今承德的东北。分兵三路,济尔哈朗与岳讬率右翼四旗攻大安口,阿巴泰、阿济格率左翼四旗攻龙井关,皇太极则由洪山口逾边墙,目标先是关内河北的遵化。
明总兵赵率教来援,兵败被杀,巡抚王元雅在城破后自尽。后金军队接着向蓟州(今河北之蓟县),至通州,距北京二十里驻军。辽西的明总兵满桂、侯世禄等俱集德胜门,崇祯元年十一月,袁崇焕由间道飞抵郊外,转战于广渠门外,急追金兵至北运河。
“上(崇祯)闻崇焕至,甚喜,温旨褒勉,发帑金犒将士,令尽统诸道援军。”这时皇太极释放那两名宦官,他们到京师见崇祯帝,崇祯帝听信他们的话,“十二月辛亥朔,再召袁崇焕于平台,遂下锦衣卫狱”。(《明通鉴》卷八十一)遂逮捕袁崇焕。《通鉴纲目三编发明》曰:
袁崇焕在边臣中尚有胆略,其率兵勤王,实属有功无罪。庄烈始则甚喜其至,倚若长城,一闻杨太监之言,不审虚实,即下崇焕于狱,寻至磔死,是直不知用间愚敌为兵家作用。古今被绐而偾厥事者,指不胜屈,未有若庄烈此举之甚者。
崇祯抓了袁崇焕以后,是否杀掉还有犹豫,这时温体仁与兵部尚书梁廷栋五次上疏请求杀掉袁崇焕,这样袁崇焕才被处死,温体仁贪赃枉法之状前已言之,梁廷栋在崇祯四年时因纳贿营私之事被人揭发而罢官落职,由此可见贪官为害之甚。
袁崇焕死后,崇祯不得不启用孙承宗及马世龙,辽将有不少是马世龙部曲,多自拔来归,祖大寿亦敛兵待命。孙承宗以马世龙总理援军,这样明军与后金军周旋至次年五月,皇太极才取道冷关口撤出关外,留阿敏守关内之永平、迁安、滦州、遵化,此四城后被孙承宗收复,阿敏狼狈逃走,后被皇太极幽禁起来。
明末杀熊廷弼和袁崇焕,是明王朝自坏长城,其根子在于明朝上下官僚系统贪污成风。这个问题从李自成进京以后,刘宗敏对明朝官僚拷掠贪官的情况,也可以看到明朝官僚系统贪污腐败之风盛行。
《明季北略》卷二十六《廿五癸丑拷夹百官》条记载:“限内阁十万,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,科道吏部郎五万、三万,翰林一万,部曹千计,勋戚无定数,人财并尽。”比较起来,对勋戚追赃更重一些,如嘉定伯周奎,“藉其家得现银五十三万,缎匹以车载之,相属于道,诸所冲积,尽搜无遗。”
又如大学士陈宾:二十七日索饷,遂举皮箱亲送宗敏家,凡四万两。宗敏喜其慷慨,不拷掠,仍系之。其仆或告贼。言:“地下有银数万。”掘之,果如仆言。又言:“珠宝最多。”复搜进黄金三百六十两,珍珠成斛。
其实吴三桂也是一个贪官,他在给父亲吴襄的第一封家书中讲到:“闻京城已陷,未知确否?大约城已被围。如可迁避出城,不可多带银物,埋藏为是。”可见其家财物甚多,由此亦可知明朝整个官僚系统无论文臣还是武将,贪污腐败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。
朱元璋下决心治贪,颁《大诰》四篇,只是收一时之效,一旦松弛,结果明朝就亡于贪官污吏之手。可见反腐斗争必须持之以恒,不能有丝毫松懈,否则就会前功尽弃,明亡的教训值得我们警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