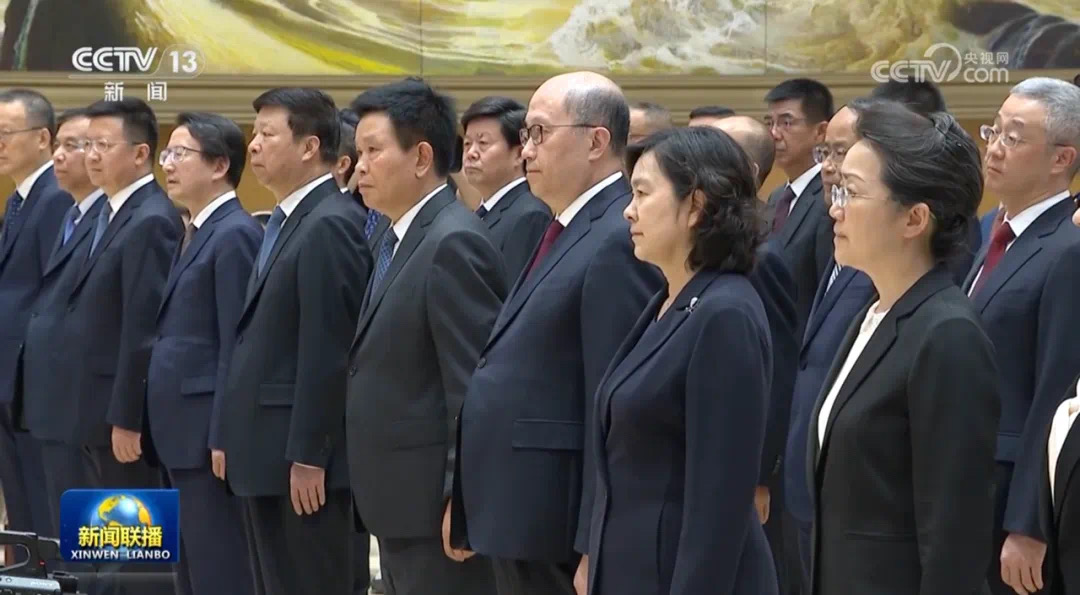江平:在沉闷的空气里,总得有人喊两声

2011年夏天,我骑车走了一趟川藏线,在路碑上看到一句永远也忘不了的留言:“只向真理低头!——向江平校长致敬。”那天中午,高原上的日光明媚得耀眼,同伴们把自行车停在路旁,席地而坐,开始吃东西或者拍照,我却对着这块路碑发了好长时间呆。彼时,我对江平知之甚少,非常好奇他有何等魔力,竟然能让人把崇敬之情带到这荒山野岭。
从拉萨回来后,我认识了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,便跟他提及此事。他表现得毫不意外,自豪地告诉我:“江平是我们永远的校长。”他说出这句话时的骄傲神情,很明显地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:江平是一位让人感到荣耀的校长。在那一刻,我突然心生嫉妒——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校长?
这位朋友生于1987年,当江平于1988年被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,他只有1岁。当他于2006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时,江平去位已有16年之久,除了偶尔听一两场江平的讲座,他和江平并无任何交集。所以,我很难想象他对江平的这种感情。还没等我问为什么,他就跟我讲了一段故事。
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运动中,当局面很紧张时,江平担心学生冲出校门后会发生流血事件,就在校门口堵学生。他对学生们说,我做校长的,要对你们的安全负责,要对你们的家长负责,你们要出去,就从我身上踩过去。
这故事听得我唏嘘不已,回来之后就赶紧查资料,知道了江平还曾和其他九位校长搞了个十校长签名,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。当北京市委开会征求十校长意见时,江平说应该跟学生妥协。而时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却说,没法退,一步都不能让。
风波发生半年后,江平就被免职了。当时尚未满30岁的贺卫方是见证者之一,他在当天的日记里,记下了江平在免职大会上做的演讲。江平的最后一句话,是这样说的:“总之,无论地位怎样变化,无论从事哪种工作,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,无愧于人民!”
所幸,一代又一代的法大学子都把江平当作“永远的校长”,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江平在学生心中的地位。
2013年年初,我和同事去参加《出没风波里:江平和他的时代》(陈夏红/著)的新书发布会。在等电梯时,一群人簇拥着江平向我们走来。他身材魁梧,头上白发稀疏,淡淡的倒八字白眉,看上去倔强而威严。
在随后的发布会上,每次记者提问完毕,陈夏红都要凑到江平耳边,大声重复记者的问题,然后江平才作答。见此情景,我心有不忍,以至于后来从未动念要采访他老人家。
江平的一生,是坎坷的一生。1951年,21岁的江平被派往苏联学习法律。1956年,他学成归国,心情激动地高喊:“啊,祖国,我回来了!”却不曾料到,厄运正等待着他。1957年,刚结婚一个礼拜,江平就被划为右派,从“人民的阵营”被划入“敌人的阵营”。一个月后,新婚妻子提出离婚,由于政治原因,江平只好同意。没多久,他在西山劳动时,又被火车轧断了一条小腿。妻离家破,腿断身残,为了坚强地活下去,他用座右铭——“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”——来激励自己,“真正的强者,不是没有眼泪,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”。
江平的一生,是为中国法学贡献的一生。他不仅在法学研究领域有诸多建树,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才。今年85岁高龄的他,还带着博士生。更为重要的是,自改革开放以来,他为法治呼吁了30多年。他并不避讳“公知”的称号,常以法学家的身份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。他尤为喜欢“呐喊”,曾有两本书的书名都用了“呐喊”这个词。江平之所以不停地呐喊,是想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,去呼吁另一种声音,“于沉闷的空气里,总得有人喊两声吧。”
2014年11月7日上午,在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的开幕式上,江平再次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。十八届四中全会把“依法治国”提到了更高的层次,确立了“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”和“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”的理念。无论如何,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。但“依宪治国”和“宪政”到底是什么关系?江平说,宪法是静态,宪政是动态的,依照宪法来治国理政是宪政的一个基本含义,所有的党政机关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,那就是宪法至上,违反宪法的错误行为都应该摒弃。台上的江平声如洪钟,台下掌声雷动。
下午,江平作为评议嘉宾,出席了“司法体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”分论坛。这个分论坛上半场的主持人是徐昕,下半场的主持人是王建勋,我是他们的学术助理。按照事先的设计,由于江平是大会开幕式的演讲嘉宾,我们就没有安排他在分论坛做主要发言了。但我们一致认为,江平作为德高望重的法学界泰斗参加分论坛,理应请他做总结发言。
上半场快要结束时,江平发言了,他说:“司法改革的关键,是让每一个具体的人,能够从法院判决的案件中,感受到正义”。但在下半场即将结束时,主持人照例请江平做总结,却被他拒绝了。从下午两点到六点,整整四个小时,江平一直安静地倾听诸位学者的发言,自己说话的时间不足五分钟。
第二天,我和几位媒体同行在江平所住的房间里,对他做了一个联合采访。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大海,隐隐约约能听到海浪的声音。采访的前一天晚上,陪同江平参会的《领导者》主编李文子对我说,提问可以尖锐点。
我问:“由于四中全会的决定过于强调党的领导,有外媒说这是中国法治的一次倒退,您怎么看这个评价?”
江平说:“我不赞成外媒笼统地把四中全会说成是倒退。依法治国的中心思想是否遭到破坏,关键不在于强调不强调党的领导,而在于强调什么样的领导。”
“问题是,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,肯定不会有公正的司法。那么,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的关系?”
“我们强调党的领导是没问题的,但应该强调党在政治上的领导,而不应当强调党对于法治的具体领导。如果党要干预司法的具体业务,那肯定是错误的。”
我仍穷追不舍,问道:“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,治理这个术语开始兴起,有人担忧法治会沦为治理的技术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,因为可能会缺少对治理者本身的规驯和约束。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担忧呢?”
“这个问题有意思”,这一次,江平笑了。“可能会有人把现在的法治,理解为治理的技术。如果真正要实现法治,那就离不开我们政治制度的改革。要实现对治理者本身的规驯和约束,就是对党的权力进行约束,这个是很深层次的问题。”
对于四中全会,江平不认为是退步,但同样也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进步。他还是和以前一样,认为中国法治的建设,往往是进两步退一步。法治的进步,只能靠一步一步积累。
新京报的一位女记者也参加过“司法体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”分论坛,很敏感地注意到了江平拒绝做总结的细节。这一次,她不失时机地问了个为什么。
江平说:“在学术界,大家都是平等的,有不同观点也是很正常,应该互相尊重。你老让我做总结性的发言,我就不愿意说了。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师,况且现在的思想在很多地方比年轻人落后了,不愿意老是给出一种结论性的意见。”
2014年,江平最大的变化,是住进了老年公寓。“当然,我的地位还没有变,仍然是学校终身教授,工作还很多、很忙,邀请我讲话的也很多。但是总的来说,还是感觉到自己是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了,这是历史规律吧。”
2009年,贺卫方曾为江平的八十华诞而作下长文,说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需要自己的脊梁,而江老师就属于这样的脊梁,法治社会的建立,靠的也就是这样的脊梁。如今,这位脊梁已经85岁了,他所希望的,是年轻一代的教授都能够坚持法治的理念。但他又说,“这并不容易。”